张炜:写一切能感动我的事
http://www.newdu.com 2024/07/27 02:07:22 天津日报 宇浩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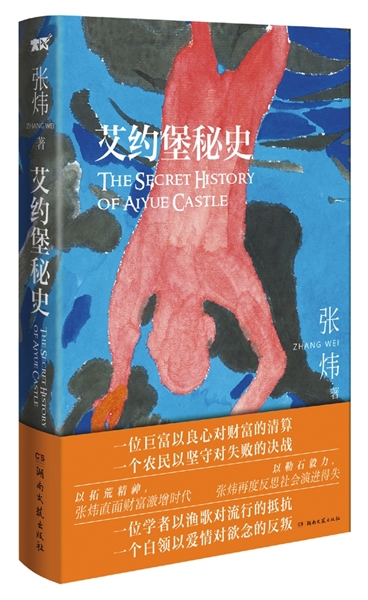 张炜, 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张炜文集》48卷,各种单行本600余部,作品被译为英、日、法、韩、德、塞、西、瑞典等多种文字。 印象 写作就像打深井 不久前,张炜再度推出了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和散文集《海边兔子有所思》两本新书。王蒙称赞他是“长篇能手”,其实张炜不仅擅长写长篇,也是精通各种文体的多面手。上世纪80年代,还不到30岁的张炜写出了轰动文坛的《古船》,此后他一直笔耕不辍,仅小说创作就有短篇130多部、中篇20多部、长篇21部,《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丑行或浪漫》《你在高原》等均为扛鼎之作,尤其是摘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你在高原》,以原稿600万字、出版450万字的体量,创下中外纯文学史的记录。 耗时22年潜心写一部作品,这事放在“死磕”文学的张炜身上,一点儿也不稀奇,因为他从年轻时就是一个为了写作可以不要命的人。《古船》的后半部分是他隐居在济南南郊一个废弃的变电小屋里写的;有一年他躲到山里写作,大雪封山差点儿被冻死,被朋友发现时已高烧3天;为了创作搜集第一手资料,他曾两次徒步冒雪翻越胶东半岛,最狼狈时衣衫褴褛,头发有一尺长;写《你在高原》时他把自己关在舜耕山背后一个废弃的工程小院里好几年……张炜毫不讳言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我曾经住过很长时间的医院,那时很孤单,心里有很多话要讲,经常卧床,对人生有感触,用托板支撑,一天只写一两行。我的感觉,要写得慢,除非不想当好作家,只要稍微看出对文字的不爱和游戏,这个人一定走不远。” 所以他对文学精益求精,《古船》写完之后改了差不多两年才拿出来发表;《外省书》光是开头就写了三十多遍;《刺猬歌》的结尾写了四十多遍;就连一篇三四千字的散文,他也会反复推敲。“我个人对文字特别重视,即便如此,回头看自己40多年的文字,有的那么粗疏,看了后悔,但当时我是倾注了全部精力的。时间,比人更智慧,标准更坚硬,对时间的敬畏和恐惧,使我不敢放松对文字的要求。” 略萨曾跟马尔克斯讲过,写作首先要想明白一个问题──你要做一个好作家,还是做一个坏作家──要不就别写。显然张炜是要做好作家的人,他把作家的创作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打深井型,一是跑马占地型,他说自己属于打深井型,抓住熟悉的生活不断往下开掘,寻找生活的意义。对他而言,但凡自己写出来的长篇,都是至少酝酿了15年的种子,“让种子放得时间更长一些,也是为了等待一些种子死亡、另一些种子萌生。这是作家的一种选择方法,等于自然淘汰法,并不是所有种子都会茁壮生长。有的种子,再厚的土层也压不住,它的尖芽会顶得人心头发疼发痒,那就是一个非要长大不可的生命了。” 文学作品还是要交给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 记者: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古船》被列为首部重点推荐,第五届评选时《九月寓言》也被一致看好,可惜最终都落选了。直到《你在高原》才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其实一直想问问您对此的感受?如果更早拿奖,对您来说,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您怎么看待评奖? 张炜:评奖是活跃文学的一种方式,可以使写作和阅读不太沉闷。在物质和商业的时代,在一部分外行那里,差不多已经把复杂的文学审美活动简化为文学评奖,就像对待体育赛事一样。文学可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种现象大致是由于缺乏文学阅读能力造成的。《古船》和《九月寓言》没有得过上面提到的那些奖,却有可能是我前期最重要的两部作品。有影响的奖项具有很大的广告效应,但它改变不了作品本身的质地。 记者:您觉得自己发挥生命能量最好的是《刺猬歌》或《外省书》《丑行或浪漫》,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古船》《九月寓言》,得茅盾文学奖的是《你在高原》,您怎么看自我认知和外界评价的差异? 张炜:我这样讲,是仅仅指自己近二十年来的写作,并不包括更年轻的时候。《古船》《九月寓言》是我比较早的作品,大致是30岁前后的创作。当年它们因为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阅读接受,大学中文系常常讲到它们,所以通常被认为是我的“代表作”。它们对我也的确很重要。《你在高原》的体量很大,写了很久,耗费精力极大,内容也非常复杂。我今后大概再也不会写这么长的作品了。再过一段时间,更多的读者可能会与作者自己在评价上趋向一致,也可能仍有较大差异,这都很正常。文学作品说到底还是要交给有文学阅读能力的人。这本来是极简单的道理,不过真要弄懂也不容易。 记者:《艾约堡秘史》首次关注中国暴富人群,《独药师》是半岛地区养生世家的传奇故事,包括之前的《半岛哈里哈气》《寻找鱼王》《你在高原》《刺猬歌》《九月寓言》《古船》等,为什么您的每部小说都会换一个新风格?您很害怕惯性写作? 张炜:一个写了许多年的作家,对自己伤害最大的,可能就是不自觉中进行的“惯性写作”了,沿用过去的生活积累和笔调,以及顺手的结构方式,轻车熟路地完成一部“还不算太坏的作品”。这对作家来说是糟糕的事情,没什么意义。文字的堆积是最无聊的事。创作是心灵的一次欣悦和感动,需要新的爆发。没有崭新的感触和经验就不必动笔。一般来说作家的表达,在总体风格上是不会改变的,但具体到每一部新作,都应该有新元素加入进来,这些元素越多越好。特别是“笔调”,它需要去重新寻找和确定。 记者:您觉得写出自己最期待的作品了吗?还有什么特别想写的吗? 张炜:我觉得《寻找鱼王》《独药师》《艾约堡秘史》这三部近作,是我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抵达的一种目标,也是我多年来的文学期待。今后特别想写的文字当然会有,那只有放在较从容的时间里去完成它们了。我会写得比较少,因为可能去写更有难度的作品。 文字的魅力无可抵挡 如果能抵挡那就不是文学了 记者:您是少有的会同时创作儿童文学的纯文学作家,写儿童文学、散文为了换换脑筋吗? 张炜:少年读者和成年读者在我眼里大致是一样的,比如他们读一本书都要觉得有趣,都要在故事中、语言中感到满足才好。文字的魅力是无可抵挡的,如果能够抵挡那就不是文学了。写出无可抵挡的文字、无可代替的文字,这是作家的梦想和光荣所在。我一直写着儿童文学,从十几岁开始,到现在一共写了一百多万字。我不是一个专门为某个读者阶层去写作的人,而是写一切能够感动我、让我心中产生写作冲动的人和故事。儿童喜欢的文字是很难写的,因为这需要直指文学的核心。我如果写出了更多让儿童喜欢的作品,就意味着自己更加靠近了文学的核心。有人以为儿童文学是“小儿科”,是玩玩儿而已,那是大错特错了。写一下就知道其难度了。纯洁的心灵会在这里找到真正的知音,而纯洁是人多么可贵的品质。各种所谓的“文学”都没有什么豁免权,都是一样的权衡标准,比如都要是绝妙的语言艺术。 记者:网络文学作品的体量都非常大,但纯文学里,只有您的《你在高原》以原稿600万字、出版450万字,中外鲜有,22年写一部书,会不会有被掏空的感觉?写作是一种输出,您会怎么让自己保持能量充盈?很好奇,您有没有灵感枯竭写不下去的时候,会怎么突破瓶颈? 张炜:准确地说,可能没有什么“网络文学”,就像没有什么“收音机文学”和“报纸文学”一样。只有文学,好的或不好的文学。网络、报纸、广播,只是不同的发表园地、发表方式而已。好的作家,无论用什么方式发表作品,都需要苛刻严谨地对待每一个字。所以只要写得很长都会很累。文学写作的难度,稍有写作经历的人都会知道。写作中谁都会被卡住,那就只好放一段时间,多想想或者一点儿都不想。到了时候,问题总会解决的。 记者: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码字的人被称为作家,您怎么看? 张炜:作为尊称,怎样叫都可以。但显而易见,“作家”“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之类,不可能是一种职业称谓。现在写作的人很多,发表的园地也很多。过去写作的人也同样多或更多,只不过发表的园地不多。但无论多与少,并不会影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的数量,他们在每个历史时期大致也就那么多,不会太多。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总是很少的,正像一个时期思想家、哲学家不会太多一样。写作是人的一种欲望和本能。谈论写作和发表,有许多时候并不是在谈论文学。有时从市场接受上看起来很“文学”了,甚至逞一时之盛,但也极有可能与文学的关系并不大。文学接受是极复杂的审美过程,不是热热闹闹的商业促销大甩卖之类。 记者:纯文学作家通常会轻视通俗文学及其创作者吗? 张炜:通俗文学的主要功用是娱乐,生活需要娱乐,只要健康就好。“纯文学”这个概念也许有问题,但我们大致知道它指的是一种诗与思、一种语言艺术,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娱乐文字是不同的。就像相声虽然不同于哲学著作,但相声也不能被哲学著作取代。各有所需,功用和价值不同,它们肯定是共存的,将被不同的人接受或推崇。 还是要鼓励阅读经典 这是民族精神成长的大路 记者:您好像比较强调作家的世界观? 张炜:人与人之间是有精神与文化视野方面的差异的,这些决定了所谓的人生境界,作家的人生境界高,不一定能写出杰出作品,但不高,大概就更难了。现在翻书,常常感到其中的人生观、价值观很成问题,许多作品努力表现、倡导的价值目标,是比较低俗平庸、有悖于人类普遍生存法则的,甚至是有害于人类生活的。但作者未必认识到这些。比如写个人奋斗,写“强者”,仅仅“接地气”,写出真实的世态与苦境情状还远远不够,还要渗透出作家本人的“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有这样高阔的情怀与觉悟才好。敬畏、悲悯与人的自我反省力,不是大而空的套话,而应该是具体的,深刻于心、于血液和灵魂深处的。不然就很容易写成不择手段的“英雄”,这种“英雄”对于人类社会是极为有害的。作家写底层奋斗的强者,尤其需要极高的觉悟力和思想力,不然就会沉浸于狭隘渺小的个人功利主义。至于对血腥暴力色情的沉湎和玩味,那就更等而下之了。 记者:王蒙老师赞您“死磕”文学,您却说年纪让体力不如当年,会有心无力,那么您之后的创作可能会无法再超越从前吗? 张炜:他是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要超越从前的作品就得花更多的时间,花双倍的力气。文学表达是极有难度的一种工作,没有多少工作比这个更难,所以写作者哪怕有一点点长进,往往都要付出成吨的汗水。 记者:您平常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张炜:平常我想尽可能地远离“创作状态”,这样就不至于伤害“文学”。文学思维在日常生活中会被磨旧,而它应该是新锐新奇的,不应该被平均化地撒在日常生活中。 记者:您说手机是损害文学的炸弹,有这么严重吗?您平常刷朋友圈吗? 张炜:一个人总是离不开手机阅读,就像离不开烟酒一样,有可能损害健康。戒掉一些习惯是不容易的。还是要鼓励纸质书和经典书的阅读,因为这才是一个民族精神成长的大路,它实在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纸质书中的垃圾当然也很多,所以才强调多读经典。人与人的文明水准及文化素质是不同的,最终是这些决定了他对书的选择。智能手机让我们接收信息变得太便利了,所以脑子总是给填满,这是太可怕的一件事。一直沉湎在电子阅读中,往往会丧失文学阅读的基本能力,最后连明显的语言优劣都看不出来了。不过从网络中看看新闻大概还行。 张炜口述 一个人不停地往下写 我有大量的精力放在写散文上,我个人最喜欢写诗,但写得不好。我的长篇小说影响超过短篇和中篇,长篇我写了21部,回头看,比我想象得好;短篇写了130多部,但出个短篇集只能选出十来个稍满意的;中篇写了20多部,个人认为稍微满意的也就三五个,回头看就是这么残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文体最难?对我来说,写长篇容易一点,短篇很难写,写诗最难。所以,我对写诗的人要高看一眼。 散文很自由,完全敞开自己,任何事情没有比敞开自己来得有意思、来得高兴,我散文的写作量比我整个虚构作品的量还要大。我所说的散文概念,是大散文的概念,不一定是我们印象中杨朔写的那类艺术散文,我说的散文边界要开阔一些,比如《出师表》是千古名篇,就不是艺术散文。我认为散文要放得开,要以不同的形式来书写自己。 我还写过报告文学,写过两个话剧剧本,没有出版,没有发表,也没演过。我觉得一个写作者不能专门写小说,不写其他,而是什么都要写一点儿。作家表达自己,需要找到一个很好的题材和体裁,题材可以四处挪换,体裁怎么不可以?我试着写戏剧或许不成功,但对自己的文字是很重要的训练和尝试。像我写的诗有可能是失败的,但我一开始写作是写诗。1975年,我十几岁时《诗刊》要发我的组诗,后来说形势变化太快,不能发了。如果能成为一个写出自己的诗人,应该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现在我每年都写诗,我觉得把热情、能力都交给诗了。 一个人不停地往下写,短篇、中篇、长篇,个人感觉好像有台阶似的,不断实现自己心中的某个追求或梦想,写了四十多年,还有没有梦寐以求的东西要写?如实说,我觉得有大量的东西没有实现,心里面有那么多东西要想写出来,一想起来会激动,但是,一是没有时间,一点儿时间没有是假的,但这些时间和心情还不足以去干那个大活,去摘下心里面最重要的果实,只好放下。二是体力,到了55岁就有这个感受,有那个心,没那个力。心里边好多让人激动的诗、长篇、散文,但是没那个体力了。 海明威五十多岁时说过一句话:当作家特别尴尬,活到五十多岁才闹明白写作那点儿诀窍,上帝却把我们的身体搞坏了,知道怎么做是好的,但是没这个力气了。我的体会和他一样。我写到2010年左右,有一天觉得有点儿成熟了,但也发现自己的力气一天比一天小,力气和时间不足以让你完成心目中最完美、最诱惑的果实。时间和精力都不够,这是作家的痛苦。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时间空下来,再一条是好好保养身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