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耐冬 节日、历史与现代
http://www.newdu.com 2025/11/12 12:11:18 经济观察报 张耐冬 参加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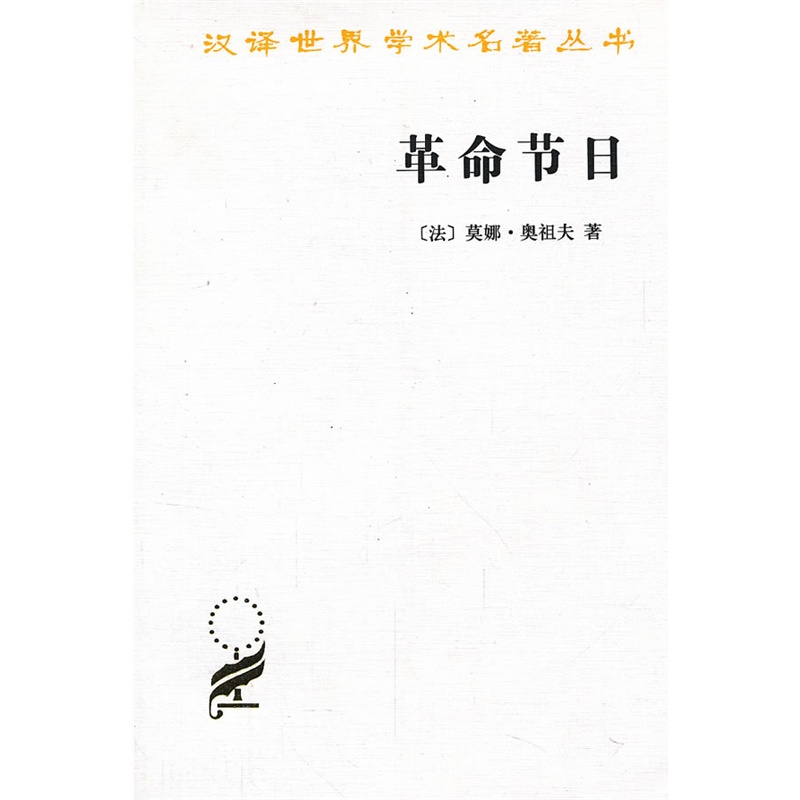 《革命节日》;(法)奥祖夫著,刘北成译 ; 商务印书馆2012年7月出版 现今,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现实,因为这正是一个各种思想热衷于设计未来图景的时刻。媒体充斥着各式关于未来的愿景,似乎我们正处于一个近似于“轴心时代”一样思想大爆炸的关键时期。而若对现实有所了解,就会发现大多数构想,诸如“儒家宪政”之类,就如七彩的肥皂泡般不堪一击。 事实是空想的克星,我们了解现实,正是为了追寻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现实并非只是当下,还包括与当下各类事实有关联的过往。司马迁所谓“述往事,思来者”,正是对历史、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联性最好的解说。 且让我们从现实中的细节入手来看。在今日的社会,很多事物对公众而言都是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比如说节日。我们对大部分节日的体认基本停留在其是否“公休日”这个关乎个人权利的层面上,而对某一节日的由来与纪念形式往往知之不详。节日与假日,在公众意识中的界限并不明显,以致关于节日的“开年大戏”成了除夕是否应该放假的争论。 法国学者莫娜·奥祖夫的《革命节日》,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代节日,进而对其进行改造,使之摆脱成为普通假日的困境。在这本书中,她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出现的节日所具有的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节日是革命者们试图对社会观念进行改造的重要形式,通过节庆的纪念仪式,对法国大革命所强调的基本思想进行不断重复,并将其具象地展现出来。节日庆典,是塑造近代法兰西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尽管其实际意义并不像革命者所设计得那样有效,但统一的国家、公民与社会这些基本观念依然依靠节日的仪式得以传播。 当大革命将法国历史划分为“旧制度”与新时代之后,如何建立新时代的纪元、如何为新时代赋予生命,是革命者们必须加以论证的。除了在演说台上侃侃而谈,节日庆典是他们教诲国民的另一舞台,甚至可以说,节日的庆祝礼仪有时比政治家的演说享有更大的舞台。奥祖夫尽可能地复原了节日舞台的形式及其背后的精神,以及对节日设计者与受众而言节日的实际效用。她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庆典与纪念有很多精彩的分析,并且直指节日背后的时代主题——对大革命而言,这些革命节日有何作用?对近代法国而言,这些节日又提供了什么?《革命节日》应该成为我们反思本国现代节日的一把钥匙,让我们认真审视现代节日所反应出的国家观念与文化意识。如果能够对现代节日与传统节日各自所拥有的文化资源以及二者在现代国家中各自所应具有的地位做系统的分析,那会是观念领域的救时之作。现代节日在国家意义上的功能弱化,与传统节日在文化意义上的强化,很容易把我们拖回到中原文化本位观念中,而中原本位的观念,很容易造成现代国家的内在分歧,即为什么必须承认中原本位是我们的国家精神。 正如传统节日与现代节日各自对应了中国在前近代时期与近代以后的文化与国家精神一样,从国家的构成而言,现今的中国也是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域在历史时期联系、结合并逐渐成为统一组织的结果。统一政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元化。传统节日也罢,中原本位的文化观念也罢,都只是中国这一政权内文化的一部分,而周边地域的文化传统,又应在国家中有何等地位? 沉醉于中原本位观念,并深受儒家或新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们似乎并不重视这一问题,然而这绝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即将迎来的春节,以及随之而来的“春运”,都只是在中原历法所规定的“元日”基础上的文化纪念和假日出行。作为一个全国性节日,对春节的宣传事实上遮蔽了非中原文化区域的节日观念。对非中原文化区域的无知,是公共领域的群体性无知。因而,有必要推荐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我们的历史讲述模式,往往将中原王朝作为重心,讲述中原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并讲述周边地域如何接受中原文化,或以中原文化为蓝本改造其自身文化。在这种讲述中,周边地域被自然或不自然地打上了“落后”“野蛮”的印记,需要在中原文化的辐射之下才得以迈入文明时代。这种观念的历史源头,是强调政治与文化“大一统”的汉代“春秋学”。 以边疆史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是拉铁摩尔不同于大多数学者的治学旨趣。脱胎于边疆学派的独特视角,让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没有落入中原文化中心论和中原文化本位的窠臼,他对中原政权与周边地域在长城沿线的边疆角逐特征的描述,以及这种角逐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的分析,都会令我们对中国历史产生与以往不同的理解。 他特别提出,草原世界与中原王朝彼此都无法真正征服对方,而两种文明在边疆地区的交会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文明秩序,在边疆地带不断扩大的时代,贮存区的新文明秩序享有者就有能力成为既可统治中原,又能驰骋草原的跨界统治者,比如唐朝和元朝的建立者。这是拉铁摩尔边疆史观对中国史进行解释的最精彩之处之一,也是突破中国传统史观的王朝史叙事的石破天惊之作。 也许拉铁摩尔的著作和当下距离相对较远,现在,周边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并如拉铁摩尔所预言的那样,正通过工业化与中原地带连成一体,密不可分。这就是现代的力量。而当我们在生产、技术与生活消费上都日渐与其他现代国家同步时,我们是否应该多问一句:我们是否已经真正走向现代? 作为2013年出版的一本新书,艾伦·麦克法兰的 《现代世界的诞生》从问世起就引起极大反响。他将现代社会定义为英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这本书最具争议之处。不过,他从英国的现代化中提炼出的各种特色,却值得我们深思。 这本书并不一定是麦克法兰最杰出的著作,但一定是他对现代化问题的学术总结。书中延续并发展了他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的基本判断,即现代的出现并非是在传统断裂下的变异,而是诺曼征服英国以后历史的自然发展。对财富的追求,对财产权的重视,对竞争意识的培养,对父母家庭的疏远以及对夫妻关系的看重,相对健康的社会下对契约与权利的尊重,等等,都构成了麦克法兰所说的“现代社会”的要素。在这其中,通过社会交往和商业活动,政治治理与法律制定,对个人意识、私有财产的保护,对权利与荣誉的推崇,应该是英国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 如果我们以此为参照,就会看到,我们生活与技术的现代化,工业与国家体制的现代化实现与否,并不是决定我们是否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最根本因素。社会观念的非现代化,每每让我们退回到近代以前去寻找精神支柱。所谓“儒家宪政”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曾以儒学为“国教”的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现实,已经证明了儒家思想作为整体化的政治解决方案的不可行,现今我们还要再次尝试,更多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满足而已。而强调前近代的社会伦理与观念,对道德建设而言或许有一定益处,对社会秩序则并无裨益。 麦克法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所列举的英国现代社会观念与社会伦理,并不一定是适用于中国的良方,但可以作为我们省视自身不足的一面镜子。经历了五四时期的激进反传统运动,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相对温和持中的处理方式,对前近代的观念加以改造而非抛弃,就比如,春节还是要过,但鞭炮则不一定非要放,也不一定要祖孙三代凑在一起熬到半夜。 (责任编辑:admin) |